——我的海洋科普之心路历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孙滨 2020-01-16 11:28
首先祝贺我们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四十年。
科学普及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于我们这个拥有近14亿国民的人口大国来说,科普事业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工作艰辛,且任重道远。
本世纪初的数年间,我曾经在《海洋世界》科普杂志做执行主编,算是为海洋科学普及做了一点点实际工作。而促使我从事海洋科普,却是有过一番难忘的心路历程。
20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在《中国海洋报》做记者的十年。
那是祖国海洋事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我供职的报社新闻部,始终是海洋新闻报道的第一线。回首几十年前的往事,感慨多多。而我国大洋多金属资源调查事业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海洋科学家和我们勇敢的船员,驾驶科学考察船一次次远赴大洋,为中国和世界做出重大贡献。这是我采写过并至今难以忘却的新闻事件之一。
20世纪末,伴随经济发展,陆地资源开始显现出严重短缺,科学调研结果向人类发出警告:仅仅有色金属中的铜、镍、钴、锰等,在陆地已面临枯竭。而海洋科学勘察也同时告诉我们,广阔的海洋洋底沉积着极为丰富的多金属结核,其中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资源量就达700亿吨!中国没有忽略科学的忠告,通过正式申请,联合国有关机构批准了我们对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海域进行多金属结合调查。中国郑重承诺:确保按期向联合国提交该矿区相关资料。由此,我国一系列大洋科学考察拉开帷幕。
然而,科学探索,征途多险。
1993年5月2日凌晨,我国执行大洋多金属结核勘探任务的“向阳红16”号科学考察船,不幸被外轮撞击而悲壮沉没!船上110位科学家和船员中,107人获救,3位海洋工作者葬身大海......目击者说,当这艘科学之舟在最后的时刻船头向上隐入大海时,被救的科学家们都哭了……
出师未捷的挫折,巨大损失的痛苦,失去战友的悲痛,让海洋科学家和船员们肝肠寸断!然而,他们没有被压垮,记得当时,首席科学家眭良仁等脱险人员曾发誓:船沉了,我们人还在!中国大洋多金属结核勘察绝不会停止,更不会倒退,大家表示,下次出海考察,我们还去!
仅仅一年后,即1994年4月8日,“向阳红9”号科考船再次出航,船上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是“向阳红16”号脱险人员,他们为了祖国的海洋科考事业,不惧生死,义无反顾,再次披挂出征。
“向阳红9”号科考船出海这一去,从4月8日到11月18日整整225天!“向阳红9”号担负的,是“八五”计划1993、1994两年度的科考任务,是用一个航次完成!这一次,他们航行3.6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地质取样1146次,获得大洋多金属结核样品2360多公斤,沉积物3000多公斤,提前15天,出色完成祖国赋予的光荣任务。
时间到了1999年。
年初,我在《中国海洋报》以头版头条发布消息:我最终圈定洋底多金属结合资源矿区,新闻说,经9个航次海上科学考察我国在东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范围,圈定了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合矿区,中国对所保留的7.5万平方公里矿区“具有专属勘探权利。在今后商业开采时机成熟时,对其享有开采优先权”。
这标志着我国已在数千米深的海洋底为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得了一处“战略金属资源基地”……
数年间,作记者的我先后以大洋科学考察为主题,跟踪报道、并撰写发表了《最后的时刻》《船沉了,人还在》《祖国感谢你们》《谈笑凯歌还》《我最终圈定洋底多金属结合资源矿区》《探求人类未来的伟大航行》等相关新闻、通讯、评论。不过,相对于海洋科学工作者艰苦卓绝的事业轨迹,我不过是那个时代海洋新闻事件的忠实记录者,当然,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二十多年,转眼过去了,每每回忆起这段采写经历,总会从中受到鼓舞。
还记得“向阳红16”号科考船沉没后,那是在在杭州,为脱险科学家和船员举办的慰问会上,大家痛哭失声的场面,真是让人撕心裂肺,他们流的绝不是惊恐的泪水,更不是为自己财产损失惋惜,而是为自己积累十几年的科研资料和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而痛心疾首。他们在九死一生之后,纷纷表示,16号船虽然没有了,可我们人还在,只要国家需要,下次考察出海,我还去!这朴素、真挚的话语,让我含着眼泪,提笔写下《船沉了,人还在》的述评:“科学之船沉了,然而,科学之魂不散!泪,不能总流,探索海洋资源、为人类造福的事业绝不会停止,更不可能中断!”
他们没有食言。尔后数年间的大洋科考航次,我多次见到“向阳红16”脱险的科学家和船员们。
那次采访经历后,我始终为海洋科学工作者高尚的职业操守所激励。有人说,中国的脊梁或许是少数人,可我见识过的,却是一个群体,一个为海洋科学事业拼命的群体!
海洋资源大调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是海洋科学家以命相抵拼出来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劈波斩浪,在广阔的太平洋洋底,最终为中华后世子孙争来一座资源宝库。
然而这一伟业,尽管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我们的公众又了解、关注多少呢?
我们开始吃惊地发现,无论是年长者还是青少年,国民中不少人中,对于包括大洋底多金属结合资源调查在内的海洋科学技术的关注程度非常低,远低于对影视歌星的狂热追捧!我国国民科学素质低下的问题,在海洋科学普及领域同样深刻地反映出来。
无独有偶。
上世纪的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
把那一年确定为海洋年,是联合国“满堂喝彩”通过定下的。咱海洋大国自然高度重视。开动宣传机器大力传播。
我随机采访,跑到首都市中心,抓住人就问,“您听说过海洋年这码事吗?”
天安门、故宫那一带,南来北往全国各地哪的人都有,其代表性可见一斑。
嘿,果不其然,各色人等熙熙攘攘,旅游团队旗幡招展,我一连三个上午,总共拽住好几十人询问:您好,这海洋年……
这么大的事,本想会得到普遍肯定,或者大赞海洋九八,谁成想结果让我倍感奚落。
“海洋年?不知道!”
“国际海洋年,没听说!”
“我们不晓得什么海洋年。”
更有甚者,一言不发,对我上下瞧瞧,看那意思是在心里说,简直莫名其妙。
唯一捧场的,是几个小伙子:
“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国际海洋年,联合国定的。”
一问,他们是连云港来北京的游客。
除此之外,被访者整齐地,明白无误地用言语、摇头、无语等丰富的表达告诉我:
“海洋年,我不知道!”
按现在的话说,我当时真的“懵圈儿”了。
本来嘛,大家来北京旅游,你非要问什么海洋之类,简直是自作多情。
回到报社,看着好几张纸的询问记录,发愁:咋办呀,这么多负面回答,怎么见报?
转念间一想,这可是真实的采访记录,至少是被访者真实表达,映衬出公众对海洋的关注度——不高!恰恰反映出国人当时海洋观念不强。于是,我大胆地交了稿子,标题就是“海洋年?我不知道!”随后发表在《中国海洋报》头版……
有感于公众科学素质低下的现状,有感于海洋科学技术被社会冷眼无视,几年后的一次竞争上岗的机会,击败其他竞选对手,加之领导信任,我出任全国唯一的海洋科普杂志《海洋世界》执行主编,开始专职从事海洋科普工作。
走马上任不久,一次读者大调查,就让我彻底地“大彻大悟”了一回。原来,我们这个海洋大国国度里,为数众多的同胞们其海洋知识是极度的贫乏,海洋意识又是如此的不堪!任重道远,这词组,用在海洋科学普及工作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海洋科普与海洋时事新闻相结合——我开始确定了杂志的办刊基调,意在紧跟海洋事业发展脉搏,有针对性地实时向公众传播普及海洋科学技术知识。数年间,我在卷首专栏连续撰写发表大量的原创科普小品,这些科普小品文尽可能地贴近大众生活,涉及海洋环境、全球气候、海洋生物保护、海洋国土开发等较为敏感话题,对此,广大读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中,有关保护海洋动物的科普文章《我不想死》让我记忆深刻。
《我不想死》创作撰写灵感源于英国一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一份报告让美国驻波斯湾海军司令部陷入了极大的困窘之中,因为他们拥有的一只最优秀的排雷高手——海豚“塔科玛”竟然在执行任务时私自“叛逃”了。塔科玛是一只大西洋宽吻海豚,在伊拉克呆上还没有48小时,就在执行第一次排雷任务时逃之夭夭。据此,我以拟人化动物语言,描述了海豚躲避排水雷危险而独自逃跑的故事。后来,以这篇科普文章为基础,我继而创作了同名动画故事片文学脚本和分镜头脚本。
(该文学脚本计划呈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以此向协会四十周年献礼)
世纪之交,集合多年来海洋新闻采写、发表的文字,我出版了《从黄土地走向为蓝色》《海洋,人类的资源宝库》科普系列丛书。
2012年,在中国海洋学会工作期间,率队赴安徽芜湖,参加第五届中国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博览会主大厅一侧,是我国神舟飞船模型;另一侧就是我们海洋深潜器蛟龙号。
当时,我建议组委会:用毛主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诗句,表现“飞天入海”,以此来反映我国巨大科技成就主题。该建议被很快采纳了……
如今,我已经退休在家。做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依然感到一种责任。
从“海洋年,我不知道”联想现在,咱们海洋事业大发展啦,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我们的远洋运输船队穿梭世界,捕鱼船遍布各大洋,我们有了航空母舰,驱逐舰……
可是,谁都知道,现如今,追逐迷信的比相信科学的人多,看风水的比钟爱科技馆的人多,关注所谓星座时运的比关心天文气象、气候变化的人多……
中国的科学普及——现在进行时……
作者姓名:孙 滨
工作单位:原国家海洋局直属海洋出版社
职 称:主任记者
职 务:《海洋世界》杂志原执行主编

本文作者 孙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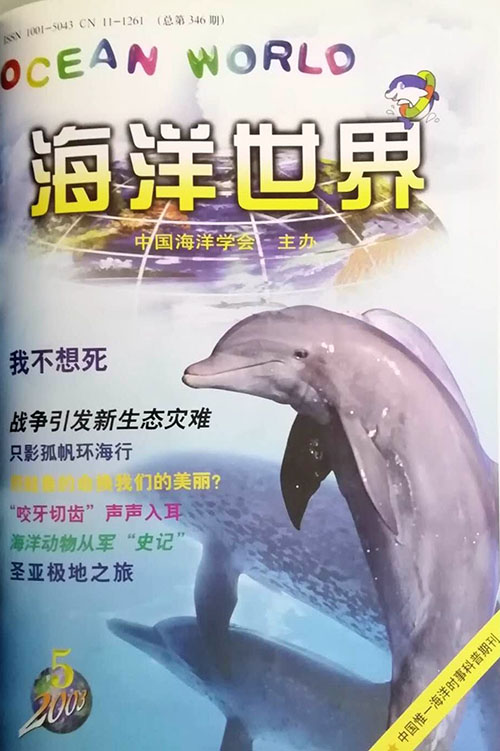
《海洋世界》杂志

我国海洋科考功勋船“向阳红09”号

被撞沉没的“向阳红16”号科考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