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最愉快的记者,是把爱好变成工作
中国记者 尹传红 2024-08-26 02:20
我是一名科技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业余的科普创作者。近20年来,我在《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科普时报》《北京晚报》《科技潮》《小康》《知识就是力量》等报刊,以开设科学专栏的形式,创作并发表了400多篇科学随笔,累计约60万字。我把这视为我的科技新闻工作和科普创作的别样表达,在这方天地上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地耕耘着,不时冒出一些思考和随想……
一、把自己的职业变成一项事业
我从事科技新闻工作已逾30年,发表了上百万字作品,科普书也出版了十几部,算是小有收获。经常有同行同事问我:记者身份和作家身份真的可以兼顾吗?
其实,记者就职业特点而言有转成作家的优势和便利,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交集就更多了。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尤其是科普文章和科学评论。例如,当年《中国青年报》上有“长知识”副刊,《北京日报》上有“学科学”副刊,《科技日报》上有“科学”副刊和“文化”副刊。这些副刊有着较为丰厚的科学文化内涵,我读得兴味盎然,当年还保存了不少剪报,以作创作镜鉴。
从一名理工男“转轨”做记者编辑,我一开始兴趣还是蛮大的,但做了十多年后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新闻是易碎品——当时觉得很重要的新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就会丧失其重要性。适逢新世纪之初,我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人生,有了更多思考。
记得有一天,我跟我的老领导、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副总编辑的王直华前辈聊天,他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来嘉勉我:“事业艺术化,人生情趣化。”我豁然开朗。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爱好来做,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有意思吗?我想,把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我期望自己源源不断出手的作品,隔了一些年头后拿出来,还是看得下去的、有价值的,可以不断地修订、再版。我将其定位为“科技新闻科普化”。
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影响很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她采访了很多风云人物,如阿拉法特、基辛格、邓小平等,以提问特别尖锐而著称。她的新闻作品集《风云人物采访记》,新华出版社很早就出了中译本,我读得特别仔细,了解到法拉奇在每次采访前,都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研究采访对象和时局形势。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拉奇既是记者又是学者,也是作家。我佩服这样的同行,视为学习典范。后来我采写报道,就总是力图在内涵深度上做文章,非常重视在采访前做功课。回想起来,新闻发布会盛行的年代,我也很少照搬“新闻发布稿”应付了事,倒时常因为案头准备充足而能写出一些“不一样”的报道,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我曾连续两次获得过中国科协“好新闻 好作品”一等奖,它们都是我在深度调研、精细思考基础上采写的长篇系列报道,且都跟科普相关。那一时期我在《科技日报》上策划的科普巨匠阿西莫夫和萨根纪念专刊、著名科学家霍金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专题报道、科学与公众科学论坛和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系列报道等,也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科普时报》版面
二、我的职业选择与科普密切相关
我在学生时代的乐趣之一,便是阅读科普和科幻作品,尤为钟爱美国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和我国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撰写的科学随笔(科学小品)。它们将我引进了科学的世界,渐渐让我体会到读书、求知、思考和钻研问题的乐趣。我对科学和阅读的热爱,伴随着学业长进,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理工科专业。那时,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科普创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
大学期间,我一边承担着极为繁杂的社会工作和学习任务,一边利用零碎的时间,结合专业学习(我本科念的是食品工程专业),坚持广泛阅读并练习写作,向报刊投稿。在大学三年级至四年级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食品报》《北京日报》《今晚报》《科学画报》等全国21家报刊上发表了76篇科普文章,这在我当时就读的工科学校里,算是比较“震撼”的事情。一时间,源源不断“漂”来的汇款单也颇为引人注目,同学们便套用当时股市中走红的“杨百万”,给我封了“尹百万”的绰号,并常常起哄让我用稿费“请客”。
而我的职业选择,也与科普密切相关。大学二年级时,我发现学校图书馆有份《科技日报》,经常刊载林自新翻译的阿西莫夫科学随笔,迄今我还记得有《黑洞》《冥王星奇趣》《艺术与科学》《致新生婴儿的信》《富兰克林改变世界》等。这些文章引发了我对《科技日报》的持续关注,并下决心毕业后“转轨”改行投奔此地。
1991年来到《科技日报》后我才知悉,林自新竟然是《科技日报》首任总编辑和社长、阿西莫夫作品中译本的第一位译者,还是一位资深的“阿迷”、多部阿西莫夫科普名著中译本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机缘巧合和对阿西莫夫作品的共同喜爱使我们成了忘年交。2002年4月,林老在纪念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及:“至于我译的几十篇短论,其中在《科技日报》工作时译的几篇在报上发表了,还为《科技日报》引来了一位‘阿迷’尹传红同志……”
数年过后,经由林老举荐,我分别担当了《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林老参与此书翻译)、《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其中部分文章正是我大学时代从《科技日报》上读到的由林老翻译的那些篇目)这两部阿西莫夫科学随笔集的编辑和校译工作,接续了老“阿迷”与小“阿迷”之间的一段故事。
我是在科普、科幻作品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走进科学世界的,如今我做的一些工作,好像都有点“反哺”的意味。就此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总结:打小痴迷科普科幻,书香悦读一路相伴;分享科学奇美理趣,留下探索思考印记。
科普的“功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引导公众欣赏科学;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如果更进一步,那就是还能传扬理性和发掘理趣。早前社会上“大师”层出不穷,每每也追捧者众,这种现象折射的不是简单的科学素养不足问题,还在于信仰、价值观与理性思维的缺失。而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盲信和荒唐来占位。如果科普作品没能吸引人或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歪理邪说就会来抢占地盘。我一直努力使自己的科普作品不仅能够正确、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而且还能向读者传递一些理性思考,以及探究事物和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
几十年来,科普一直让我乐此不疲,并且成就了我的第二事业和第二人生。以此而言,我是很知足的了。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已被看作是实现创新发展之两翼的今天,我更有一种使命担当感,期待自己能够做好科学传播的“中介”,并且在科普创作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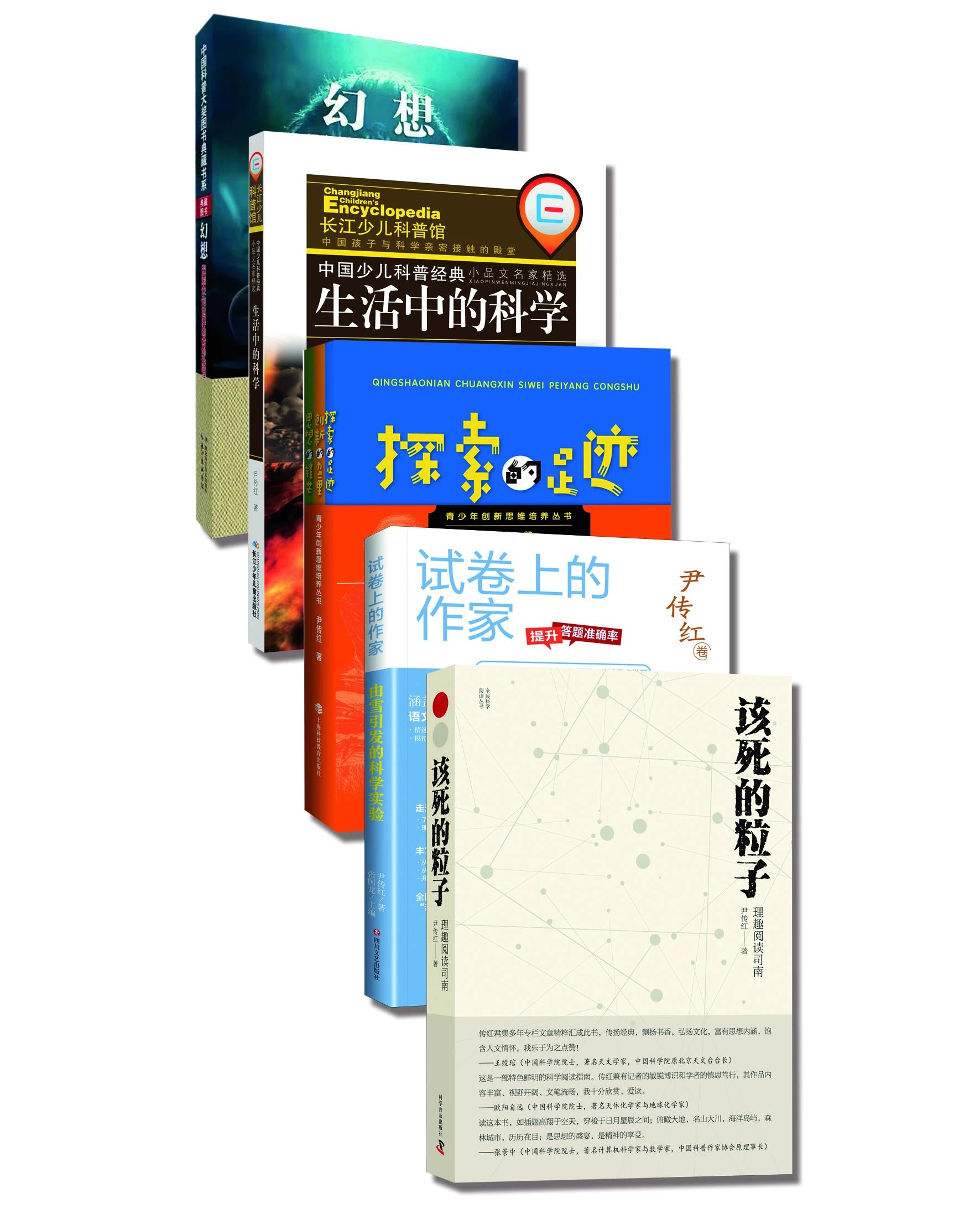
尹传红部分科普作品
三、感悟“文字有味,科学真美!”
“从阿西莫夫身上,我们学到以乐观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如果我们小时候读的科学课本能写得像阿西莫夫的文章一样,今天或许就不会有‘科学盲’或‘科技恐惧症’的问题了。”台湾省20多年前翻译出版的一部阿西莫夫科学随笔集的封底,印有这样一段宣传文字。
我读后十分感慨,并延伸了更多的思考:我们写的东西,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像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那样简洁、晓畅、明白,而不致给读者带来什么阅读障碍?我们做的科学报道,能够架起一座在科学和公众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桥梁,进而引发公众认识理性思考的真义吗?
我从对阿西莫夫作品(尤其是他的科学随笔)的研读中,吸取了许多知识和养分,借鉴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也特别欣赏他那种非常平实的写作风格。2019年我给自己新出版的“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丛书”所写的题献,真切表达了自己对阿西莫夫的感激与感恩之情:在我求知若渴的当口,你给我阅读的酣畅、理性的滋养;在我迷惘彷徨的时候,你是我人生的坐标、精神的向导。
在阿西莫夫的诸多作品中,发表在报刊上的科学随笔(Science Essay)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风格独特、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从当代社会现象着眼,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科学与人文背景。他不仅在普及科学,还努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促使人们去考虑人类与科技、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考虑人类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启迪人们扩大视野,创造性地思索未来,向未知的领域拓展。
阿西莫夫作品(尤其是科学随笔)的写作风格鲜明还在于,他始终注意营造一种跟读者的亲近感。读他的作品,你感觉到他仿佛是在跟你聊天,而不是对你说教,正如阿西莫夫著作《终极抉择:威胁人类的灾难》译者王鸣阳先生所言:“与其说他是在告诉你‘有什么’,还不如说他是在引导你‘分析什么’。”于是你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就“参与”进去,同作者(更严格地说是同科学家)一起进行分析和推理,讨论种种可能性,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阿西莫夫笔下,文字有味,科学真美!这也正是我特别期望自己的创作能够达成的目标水准和传播效果。
机遇来了。
2005年春夏间,我当时的上级、《科技日报》社长助理兼“经济特刊”主编李钢在酝酿报道创新和版面改革时,对科技报道跳不出“就科技说科技”的小圈子不甚满意,他后来找我谈话,直接提出我这个副主编要给大家带个头,在报纸上开设个人专栏《科学随想》。
多年以后,李钢在给我的作品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所写序言中提到,当年我虽然是被他“逼”着“赶鸭子上架”,但想必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这当然首先是为了读者,然后就是培养人才。不过,当初我确实毫无思想准备,也没那么大的底气。
《科学随想》专栏以《我们要不要科学偶像》开篇,陆续又推出《倾听“大爆炸”的回响》《个人化的战争》《捕鲸的“科学”理由》《游走于科学与政治之间》《干细胞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规划”出来的悲剧》《造个智能机器有多难?》等篇章,从标题就可看出文章内容庞杂,行文多有思辨色彩。因为它们大多是从时效性很强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落笔,引发思考与畅谈。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我把它们划分在了六大板块,分别是:科学探索、生命沉思、世相观察、思辨空间、人物轨迹、未来畅想。
这样,在2005年7月至2007年5月的大约两年时间里,我在《科技日报》《科学随想》专栏上发表了86篇作品。这些文章刊出后,陆续获得一些反馈,不乏热情的褒扬和鼓励。
尤为令我感动的是在南方工作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至今还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陶维正。他来信对我的专栏文章表示肯定和欣赏,还对专栏的写作定位和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冀望我能够向科学文化评论方面发展,并且提出:评论家的手笔,应有客观独到的立论、超凡脱俗的视角、透彻精辟的分析、清新优雅的文风。对此我非常赞赏。我给自己所定位的“业余角色”是:以科学随笔解读科学事件或科学话题,努力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理性的思考者、审慎的判断者、沉稳的剖析者。
2009年2月,我应《北京晚报》之约,开设了《身边的科学》专栏,每周写一篇有新闻由头的科学随笔,以科学视角解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或现象。创作中我更加注意文章选题的新颖性和趣味性,也更有兴致从科学、人文的视角去审视和考量一些社会、科学事件,乃至人物与人生。这些文章发表后反响也不错,不时有篇目被报刊网络转载,并多次被评为《北京晚报》好稿,令我颇受鼓舞。
我在打造科学专栏、创作科学随笔方面所做的探索尝试,近年来陆续结出了硕果,让我也备感欣慰:2018年1月,我在由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典赞·2017科普中国”活动中,被评为“十大科学传播人物”。2022年6月,我的科普作品出现在高考试卷上:我发表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一篇科学随笔《由雪引发的科学实验》,被用作2022年全国语文高考乙卷实用类文本阅读材料。

尹传红入选由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典赞·2017科普中国”之“十大科学传播人物”颁奖现场(摄于2018年1月29日)
四、做一个“中介型的理性思考者”
英国皇家学会于1985年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提出:各种传媒,尤其是日报,在传播科学方面大有潜力。而专栏文章有着特别的价值,因为科学本身并非总能成为新闻,专栏这种形式为科学报道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表达空间。
回头来看,当初我承接开设科学专栏的活计,一方面自是兴趣驱使,一方面也可说让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得到了“升华”。借此也开拓出一条新闻与科普相结合的新路,促使我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思考了许多问题,并有意识地探索了一种通俗化、趣味性的表达方式。
可真正做好并不容易。
首先,作为报纸专栏文章,字数受到限制,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规范,但对作者的文字功力提出了挑战。很惭愧,我一直还未能做到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因而常常留下遗憾。
在具体操作中我有时候会“投机”一下——只是选取话题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展开“随想”。而《科学随想》栏题本身,设置的时候便考虑过其归栏文章,既可以谈很庄重的话题,引人深思,也可以聊很有趣的事情,令人愉悦。无论如何要能写得到位,乃至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这应该成为专栏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甚至标准。
有一次,我的《科技日报》同事、广东记者站站长左朝胜来坐,我向他谈起自己的一些困惑,他却道:“《科学随想》这个栏题甚好,让漫思行文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他还提醒我不必采取大而全或面面俱到的写法——从某一个侧面“随想”一下也不错。我忽然就开窍了。多年之后的一天,当我与科普同行探讨科普文章的创作技巧和科普讲解的话题切入时,猛然意识到,所谓的“小口深挖”创作法,与那侧面“随想”一下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口深挖”是说,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切入点,只有将此点讲深、讲透,才能真正起到传播科学知识的效果。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或科普主题的内容“多而全”,未必合宜。其实,考虑到人们学习时间的碎片化、不确定性以及不连续性,不是知识越多越好、要点越全越好。如果每次的学习内容相对独立和短小,即每次聚焦一个科学主题,效果可能反而更好。
例如,在进行糖尿病的科普时,不再按照传统方式将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病因、症状、诊断、治疗等进行系统讲解,而是将其分成若干系统的短篇,选择大众感兴趣的热点内容,进行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阐述。这些分散的“单元”有如:《肥胖与糖尿病的爱恨情仇》《并发症,糖尿病人的生死之敌》《这样,才是糖尿病病人该做的》……这恰恰是科学专栏中的科学随笔和科普讲解这种传播方式所擅长展现的。
专栏文章的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磨练和激励。老话讲,你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就得挑一担水。说的其实就是积累问题。在“思考的笔”背后,我下的无非是笨功夫:大量阅读,深入思考。我设想,写一个领域的话题就等于是进行一个方面的学习。其实,“操练”一段时间后,选题倒是不愁,伤脑筋的是表达方式和思想的提炼。这也是当下许多文章所欠缺或做得不够,因而不太吸引人的方面。

2015年8月15日晚,国内首档全民益智科普知识电视大赛《顶级对决》登陆江西卫视。王渝生(中)、阿忆、尹传红(右)于第二现场观战并作即时点评
6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当今哲学的任务》中写道:“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想,对科学当也作如是观。我很希望可以像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那样,“能够对看似稀松平常而且枯燥无味的小事进行深刻剖析,并从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启示”。我也很佩服她“不是以日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跨越世纪的普遍真理来诠释这个世界”。
“诠释”实际上往往由“中介”来担当。对于这个角色,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曾经说过,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是无可替代的“第一发球员”,科普作家则可视为“二传手”。香港的传媒人梁文道也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像我们这种做媒体的人就是一种中介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许不是在观念上、思想上、学术上有创造力的人,不是最原创的人,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第一线的研究工作,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浏览人家的研究成果,然后把这些研究成果以我们为中介再转达出去。
如今,我在《科普时报》上仍坚持每周写一篇《科学随想》,已发表了227篇(截至2024年8月2日),职业兴趣驱使之外,也当是对自己思想和笔头的一种磨砺吧。
我愿做一个“中介型的理性思考者”,一直“随想”下去……。(作者系科普时报社社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科普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