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幻动态】过去与未来:试论法国科幻文学与科普教育
世界科幻动态 消息 2025-08-01 13:37
法语《科幻研究杂志》(Res Futurae)于2012年创刊,这是法国本土科幻研究体系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刊十余年来,该杂志开展了多视角、跨学科和国际化的研究,其研究方向涉及科幻的诗学与理论研究、媒介研究、作者研究和历史与国别研究等多个主题,每年发行两期线上开放获取的主题专刊,逐渐成为法语学界最活跃的科幻学术中心。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幻这一文类的写作方法与诗学逻辑的深度与复杂性,《科幻研究杂志》的第23期专刊于2024年6月上线,着眼于科幻的“用途”,希望通过这期题名为《科幻文学的教学意义:教育、学习与传承》(Enjeux didactiques de la science-fiction : enseignement, apprentissage, transmission)的专刊,“既聚焦于科幻本身,又关注其应用”,探索“如何教授科幻文学”和“如何通过科幻进行教学”这两个问题[1]。
一、法国科普与科幻简史
在2018年出版的法国科幻百科全书《复古科幻:法语理性推想小说百科——从拉伯雷到巴雅韦尔(1532—1951)》(Rétrofictions. Encyclopédie de la Conjecture Romanesque Rationnelle Francophone, de Rabelais à Barjavel, 1532-1951)中,编者将法国与美国流派的“科幻”术语之争放置一旁①,选择了“理性推想小说”这一外延更为广阔的名称来总览文类。正如其副标题所示,本书将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传》②定位为法国科幻史的起点[2],这部充满奇幻元素和夸张讽刺的荒诞笑剧乍一看同科幻相去甚远,但正如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认为拉伯雷的写作中蕴含着现实主义的基础因素[3],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幽默哲思也为现代科幻埋下了种子。通过描写庞大固埃对知识的渴求,拉伯雷宣扬了人文主义者重视全面性和科学性的教育观,同时,作者对主人公“奇妙历险”的刻画建立在医学、解剖学、天文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基础之上,《巨人传》在宣扬“科学思维”的同时,也是科学与虚构写作的一次精彩碰撞[4]。
在法国,“科普工作者”(vulgarisateur)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才成为专门的职业,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迎来科普的黄金时代[5],这也与法国科学推想小说的繁荣与黄金时代基本重合。在此之前,法国的科普工作与科幻创作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传统,两者的发展呈现出相辅相成的趋势特点。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讽刺小说《月亮世界的滑稽故事》(Histoire comique des É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 1657)和伯纳德·博弈尔·德·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天文学著作《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时常分别被视为最早的法国科学推想小说和科普作品。这两部作品均以天文学为主题,热烈拥抱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果,贝热拉克的文笔幽默辛辣,通过幻想地月旅行来进行社会批判,丰特奈尔的语言轻松优雅,借助六堂简明的科学课,宣传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说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科学方法论,两部作品在当时都获得了较大成功。
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时代,推崇理性的启蒙哲学家们将承担起科普创作者的工作的重任。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虽然兼容并包、卷帙浩繁,其目标读者却是“有才华、有品位、有智慧”的少数人,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普作品,不过“百科全书派”传递出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伏尔泰,这位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科普与科学推想小说作者。伏尔泰(Voltaire)在流亡英国期间接触了牛顿(Issac Newton)的理论,后撰写了《牛顿哲学原理》(É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 de Newton,1738)一书,这是最早向法国社会介绍牛顿学说的作品之一。同时,他的哲理小说《小大人》(Micromégas,1752)被视为法国科学推想小说的早期奠基之作,作者借外星人的视角观察地球,从而批判了人类的无知与自大,《老实人》(Candide,1759)则继承了欧洲文学的乌托邦写作传统,以黄金乡的完美反衬出现实世界的混乱与残酷。
启蒙运动向往的理性与秩序并未为法国社会带来安宁和稳定,在接下来的大革命时期,法国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科学热”。发展中的科学和技术与新兴的新闻媒体相遇,在法国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有关胚胎学说的论争,还是考古学的新发现,都通过报纸和宣传册等媒介几乎不加辨别地迅速传播给大众,一些已被现代科学证伪的伪科学学说也是如此,颅相学、手相学、动物磁气学说等理论在18至19世纪都有着大量的拥护者[7]。这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在现代读者看来介于“科学”与“奇幻”之间的推想作品,媒体作为科普的主力,也时常与官方科学机构就何为“科学”的定义权展开辩论③。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t,1835)、《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ët,1842)和《邦斯舅舅》(Le Cousin Pons, 1847)等作品中都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理论,其写作追踪最新的科学进展与社会新闻,既评论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与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介绍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和梅斯麦(Franz-Anton Mesmer)的神秘学理论,这种整体论的态度使得其作品中的科学形象时常显得复杂难解、晦暗不明。
伴随着现代科学的体系化与大众传媒的繁荣,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的科普创作与科学推想写作双双迎来了其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法国诞生了专职科普工作者和科幻作家,出现了专业的科普杂志和出版社,世界博览会成为影响最大的科普活动。路易·菲吉耶(Louis Figuier,1819-1894)和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分别是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不过最成功地将科学的严谨性与文学的想象力结合在科普与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人是法国天文学会首任会长卡米耶·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他出版著作超过五十余种,科普作品《大众天文学》(Astronomie populaire, 1880)和科学推想小说《世界终结》(La Fin du monde, 1893)等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虽然法国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科幻的“法国流派”仍有争论,19世纪下半叶法国确实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推想小说作家,除了凡尔纳之外,弗拉马利翁、阿尔伯特·罗比达(Albert Robida,1848—1926)、保罗·迪瓦(Paul d’Ivoi, 1856—1915)和大罗斯尼(J.-H. Rosny aîné,1856—1940)等作家不仅创作颇丰,彼此之间亦有写作方面的交流。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自20世纪初开始写作的莫里斯·雷纳(Maurice Renard,1875—1939),其《勒恩博士:类神者》(Le Docteur Lerne, sous-dieu,1908)和《蓝祸》(Le Péril bleu,1911)等作品都已成为了无可置疑的法国科幻经典。雷纳不仅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亦是法国第一位科幻理论家,雷纳用“科学奇幻小说”(merveilleux scientifique)这个名称来形容威尔斯(H. G. Wells)、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和大罗斯尼等“前科幻”作家的作品④。在他的论文《论科学奇幻小说及其对进步观念的影响》(“Du roman merveilleux-scientifique et de son action sur l’intelligence du progrès”, 1909)中,雷纳不仅梳理总结了科学奇幻小说的历史和文类结构特点,还谈到了科学奇幻小说的作用。雷纳认为该类作品不仅可以传递准确的科学知识,还会对其进行形而上的探讨,最终影响大众对于科学进步的认知观念,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受限的视角,将“未知”和“不确定”展现在读者面前[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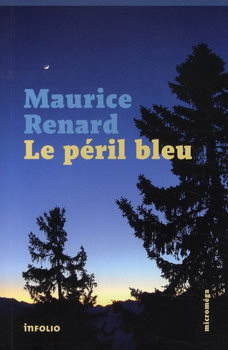
莫里斯·雷纳《蓝祸》(图片来源:nooSFere.org)
虽然法国最早的科幻理论文献已经提到了科幻的科普与教化作用,但当代法国科幻研究者却从未格外关注科幻与科普之间的关系,甚至长久以来,科幻研究、科普研究和科幻教学似乎属于毫不相干的领域。《科幻研究杂志》的第23期刊物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并与美国《科幻研究》杂志1996年的特刊《科幻在学术界》(Science Fiction in Academe)形成呼应。本期刊物转载并翻译了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的《教授科幻》(“Teaching Science Fiction”)和芭芭拉·本格尔斯(Barbara Bengels)的《在大学教授科幻的乐趣与危险》(“The Pleasures and Perils of Teaching Science Fiction on the College Level”)两篇文章,分享两位美国学者三十年前的教学经验。该刊收录的其余八篇文章则从教学法、教学实践和语料分析等多个角度,来回答“如何教授科幻”和“科幻能够教授什么知识”的问题。
二、 如何进行科幻教学:在语文课与批判性教学之间
菲利普·克莱蒙(Phillipe Clermont)对1970年至今法国科幻小说教学的历史性研究指出,科幻小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法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了法语教学的文本素材。1979年,皮埃尔·费朗(Pierre Ferran)主编的文集《通过科幻小说教授法语》(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par la science-fiction)出版,同年,科幻小说第一次成为法语教学研究期刊《实践》(Pratiques)的研究对象,初步确立了在基础教育体系中讲授科幻小说的教学法原则。卡尔·康瓦特(Karl Canvat)于1991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法语教师手册》(La Science-fiction, vade-mecum du professeur de français)节选了凡尔纳、阿瑟·克拉克、勒古恩等作家的15篇科幻小说,作为中学科幻教学实践的范例。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教师将科幻小说视为中学常规教学实践的一部分,法国教育部公布的法语课程教学大纲中也加入了不少科幻小说,在2007年教育部的450本推荐阅读书目中,有33本属于科幻小说,作者调查的40本法语教材中也有一半收录了科幻小说。在这些教材中,科幻文本通常被视为法语写作的教学工具,用于教授初中低年级的叙事文写作和描述性写作,以及高年级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写作等[9]。
在另一篇文章中,克莱蒙分析了科幻给中学生读者带来的阅读挑战及其教学潜力。从对学生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来看,对于中学生来说,科幻并不属于可读性强的文类。作者认为科幻文学具有对读者要求高、互文性强和语义陌生性较高等特点,这使得科幻有利于培养谨慎、客观、思辨性强的读者。目前已有一整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可以用于课堂上对科幻文学的分析,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工具和路径[10]。
杰拉尔丁·维肯斯(Géraldine Wuyckens)从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的教学实践出发,分析了该设计方法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设计虚构是一种利用科幻来想象技术未来发展的设计方法,最初主要被应用于传统设计和人机交互设计领域,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将其定义为“有意使用故事原型来悬置对变化的怀疑”[11]。如同科幻小说一样,该设计方法也强调认知陌生化的重要性,也时常从科幻作品中汲取美学灵感。作者与比利时非盈利教育机构Action Médias Jeunes合作,开展了为期五年的批判性思维教学项目。该项目的学生以小学生和高中生为主,教师引导学生以未来发明者的身份思考,通过创作科学推想性场景,讨论未来的可能性。作者认为设计虚构和科幻作品都能够超越作品本身,鼓励学生反思现实以应对未来的挑战[12]。维肯斯还与马丁·拉隆德(Martin Lalonde)合作,将虚拟现实(VR)引入魁北克高中的视觉与媒体艺术教学实践中。研究者邀请学生想象千年后的未来世界,并借助VR的技术支持,创造出沉浸式的叙事体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模式深受电子游戏和科幻电影等流行文化的影响,VR提供的沉浸式交互框架可以轻松与他们产生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思辨能力[1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语世界的科幻教学从仅关注科幻的文学性变得更重视其跨媒介的文化维度,科幻现在不仅视为语文课的阅读材料,更成为培养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的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目前法国的科幻教学还仅限于基础教育阶段,并未深入高等教育体系,法国大学的文学院中极少开设科幻研究相关的课程。同时,中学科幻教学中也存在着困难。菲利普·克莱蒙指出,科幻这一文类作为正当教学内容的合法性近年来才逐渐被艰难地建立,虽然将科幻看作“有关科学的小说”来教学的可能性绝对存在,如何在教学中落实科普教育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14]。
三、科幻如何作为教学工具:作为知识传播载体的科幻
艾丝黛尔·布朗凯(Estelle Blanquet)和埃里克·皮勒肖(Éric Picholle)尝试将科幻带入天文学的课堂。作者指出,现代天文学的历史时常被简化为两个重要时刻:哥白尼革命和伽利略对教会蒙昧主义的挑战。然而,天文学的真实历史实际要更加丰富和微妙,并且始终与其时代的科学想象保持互动。作者选取了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格雷格·伊根等作家的科幻小说,以及现代早期的科学推想作品选段,试图从科幻小说提供的历史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天文学的发展史。由于科幻作者们善于在历史写作中另辟蹊径,他们为读者提供了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助于学生识别固有教学模式的过度简化所带来的问题。与此同时,教师的任务是借助科幻构建一种教学机制,促使学生采取假设—演绎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得学生能够超越权威的论争,更好地理解学习中碰到的问题[15]。
天体物理学家、《通过〈星球大战〉学习科学》(Faire des sciences avec Star Wars)的作者罗兰·勒胡克(Roland Lehoucq)分享了科幻在其科普分享工作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科幻能够直面科学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反思现代科技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因而可以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和培养科学思维的工具。文章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分析了通过科幻文本中的情节和设定引发科学问题并进行探究的两种方式:一是辨别作品中的科学成分是否可能或合理,二是基于虚构作品假定的科学规律深入挖掘文本中未明示的信息。作者通过科幻电影的实例(如《星球大战》的光剑和《阿凡达》的行星系统)展示了如何将虚构情节转化为科学探索,他认真对待虚构世界和新物理规则的构建逻辑,并提出了一种将科学与流行文化结合的教育策略,用游戏的方式引导听众产生对现实的陌生化理解[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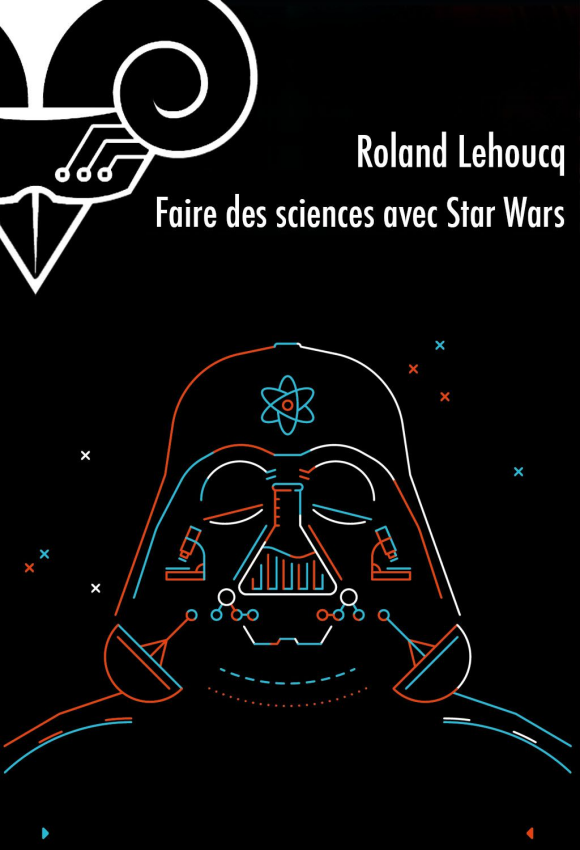
罗兰·勒胡克:《通过〈星球大战〉学习科学》(图片来源:Le Bélial)
塔蒂雅纳·德罗伯特(Tatiana Drobot)和阿莱克西亚·金冈德(Alexia Jingand)的论文分别从具体文本出发,分析了科幻作品的教育意义。德罗伯特分享了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e Bogdanov)的科普观和教育理念。其科幻作品《红星》(L’Étoile rouge,1908)和《工程师门尼》(L’Ingénieur Menni,1912)构建了两个道德观、认识论和知识状态相互对立的世界,主人公所经历的文化和政治革命,都源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碰撞。波格丹诺夫的作品具有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特点,通过描写各种学习情境和学习者,他的小说成为了思考学习与知识传递问题的有效场域。通过其思想实验,波格丹诺夫展示了文学文本在教学能力上的局限性。他在强调科幻小说的教学和认识论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它所面对的语言局限,由于科幻的语言始终游移于科学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之间,必然会导致社会语言学相关的理解问题[17]。
阿莱克西亚·金冈德则基于杰克·万斯(Jack Vance)的《帕奥的语言》(The Languages of Pao, 1958)、阿尔及利亚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的《2084:世界的终结》(2084 : La fin du monde, 2015)和东德作家约翰娜·布劳恩和君特·布劳恩(Braun Günter et Braun Johanna)的《超越球形的计划》(Das kugeltranszendentale Vorhaben, 1983)三部反乌托邦小说,建立起了一个外语教学的语料库。这些作品中描绘的语言教师和学习者形象呈现出某些关于教学法的共同特征,值得进行定义和分类。基于语言相对主义和非正式学习的教学法,研究者关注与语言教学相关的想象的词汇,提出更深入的问题,例如:学生学习哪些语言?教师如何接受培训?教师职业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制度化并具备社会声望?学生是否是教师的“囚徒”?受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的启发,作者提出与传统的教师-学生-知识三角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型,希望通过推广非正式学习,将学生置于教学核心,使得学生更积极主动地获取自己选择的知识,而非由权力强加的知识[18]。
四、结语
法国学者总结了法国科幻教学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了将科幻视为教学工具和学习场所的可能性。这一期刊物集合了科普工作者、教师与科幻研究者的对话,超越了《科幻研究杂志》以往只重视科幻的诗学、美学和文学史价值的视野,从其实际功用出发,展示了科幻与教学实践、新媒体和新技术结合的巨大潜力。
作者简介:
朱欣宇,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索邦大学法语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1800-1939的法国科幻与科学史。
① 在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于1929年提出“science fiction”这一术语之前,法国出版界已出现“科学小说”(roman scientifique)、“科学预想小说”(anticipation scientifique)、“科学假想小说”(roman d’hypothèse)和“科学奇幻小说”(merveilleux scientifique)等多个术语来指涉科幻小说。为了与美国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区分开来,部分法国学者采用“推想小说”(fiction spéculative)的说法来指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被全面引进法国之前的本土科幻作品,为避免术语的混淆。本文也将保留这一用法,用“科学推想小说”来指示二战前的法国科幻作品,“科幻小说”则用来说明二战之后的作品。
② 《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作家拉伯雷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一共有五卷,讲述了巨人国王卡冈都亚(Gargantua)及其子庞大固埃(Pantagruel)的神奇事迹。
③ 17世纪大革命前法国受官方承认的科学机构有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皇家医学会(Société royale de médecine)和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等学术机构。
④ 雷纳于1909年首次提出“科学奇幻小说”的概念,在1928年又采用了“假想小说”(roman d’hypothèse)的说法,这两个词汇的外延大概一致,都可以用来指涉19世纪以来的“前科幻”作品。
参考文献:
[1]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Res Futurae. « Éditorial n°23 » [J/OL]. ReS Futurae, 2024-06-25 [2024-12-14].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460.
[2]Guy Costes et Joseph Altairac. Rétrofictions. Encyclopédie de la conjecture romanesque rationnelle francophone, de Rabelais à Barjavel, 1532-1951 [M]. Amiens: Encrage, 2018.
[3]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M].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4]拉伯雷.《巨人传》[M].鲍文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Guy Vautrin. Histoire de la vulgarisation scientifique avant 1900 [M]. Paris: EDP Sciences, 2018.
[6]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M]. Paris: Éditions Flammarion, 1993.
[7]罗伯特·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Maurice Renard. « Du roman merveilleux-scientifique et de son action sur l’intelligence du progrès » [J/OL]. ReS Futurae. (2018-6-20) [2024-12-14].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201.
[9]Philippe Clermont. « “Enseigner avec la science-fiction” : quelqu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récente de l’enseignement de la science-fiction en France (1970-2020)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2].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360.
[10]Philippe Clermont. « Lecteur méfiant de science-fiction et développement de savoir-faire en lecture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5].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333.
[11]安东尼·邓恩,菲奥娜·雷比.《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M].张黎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
[12]Géraldine Wuyckens. « Le potentiel éducatif du design fiction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ensée critique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5].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267.
[13]Martin Lalonde et Géraldine Wuyckens. « Des lendemains incertains : immersion dans l’imaginaire du futur des adolescents. Étude sur l’intégration de la science-fiction et de la réalité virtuelle en enseignement des arts dans les écoles secondaires québécoises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5].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363.
[14]Philippe Clermont. « « Enseigner avec la science-fiction » : quelqu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récente de l’enseignement de la science-fiction en France (1970-2020)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4].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360.
[15]Estelle Blanquet et Éric Picholle. « De L’Histoire véritable au boulet de Jules Verne : une histoire science-fictionnelle des paradigmes astronomiques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4].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210.
[16]Roland Lehoucq. « Utiliser la science-fiction pour partager les sciences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4].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113.
[17]Tatiana Drobot. « Penser la rencontre de visions du monde plurielles à travers le didactisme de la science-fiction d’Alexandre Bogdanov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2].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163.
[18]Alexia Jingand. « Les imaginaires de l’enseignement et de l’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dans trois romans de science-fiction dystopiques » [J/OL]. ReS Futurae. (2024-6-25) [2024-12-15].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resf/13073.
刊发于《世界科幻动态》2024年第4期。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