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信息(上)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詹克明 2018-09-20 10:09
何为人类?人类何为?这或许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追问。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人问》,本篇似可视为《人答》。
从太空俯瞰地球,长达近40亿年的冥古宙、太古宙以及元古宙都如同火星表面一般洪荒一片①。只是在最近的4.1亿年,地表才因陆生植物的大发展而开始变绿,大气也因氧气的出现而变蓝。然而,在近几千年,尤其是最近500年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后,地球上鲜明地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仍是自然界,另一个则是人工界。从太空摄影可以看到,除了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冰盖雪峰、沙漠冰碛,冻土荒原,几乎所有陆地都布满了农田牧场、都市街区、海港码头、公路网络、产业基地,以及随处可见的机场、桥梁、水库、人工湖……夜晚从卫星上遥望大都市繁华地区更是灯火一片,那是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
为什么会有两个“造物主”?在地球上,年轻的人类造物主凭什么能与大自然造物主平分秋色?这是因为现代人类有语言、能思考,可以掌握科学、改变世界。一言以蔽之,作为立足之“基点”,我们拥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智能信息。
人体如“皮囊”,信息如“灵魂”。
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由原始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可谓变化剧烈,然而就人体结构而言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改变了的只是在人们头脑中所充填的“信息”。倘若古人能复活,同样的身体智能条件,给秦始皇充填马克思主义,他就是伟大导师;给李白充填相对论,他就是爱因斯坦。人类文明进步到哪个阶段,实则取决于人类掌握信息达到了哪个阶段。
直立行走诞生了现代人类
人类的直立行走是从“猿人”踏入草原开始的。400多万年前第一批两足“类人猿”进入草原,半人高的荒草使得它们必须直起身来才能观察猎物、防范天敌,为此也就逐渐养成了直立行走的习惯。与一些动物偶尔也能直起身子、步履蹒跚地迈上几步截然不同,人类的行走是建立在彻底改变人体结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原始人类颅骨中的“枕骨大孔”位置移到了颅底中央(猿类的孔则开在颅底靠后的位置)。脑袋直接坐落在脊柱顶端,显然这样安置最有利于身体直立。除此之外,直立行走还调整了人体内脏的悬系方式,加强了内脏隔膜的承托,扩展了骨盆,平展了肩宽(此项变化使得所有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可以仰天平躺)……这些都为创立人类文明提供了最适宜的身体构建。
直立行走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在于脚的结构。人在走路时,方寸大小的“脚跟”承受着全部的身体重量,久而久之,脚跟的硬皮与脂肪构成了一层厚墩墩的“吸震垫”。此外,脚部还拥有人体中最为坚韧的韧带,其中又以连接7块“跟骨骨骼”的韧带尤为强韧坚固。此韧带将跟骨骨骼牢牢地包裹在一起,以强化脚的稳固性。人的双脚有52块骨骼,双手有54块骨骼。在人体总共206块骨骼中,手足加起来共有106块,占了人体骨骼总数的一半还多,可见手与脚对人类的重要性。
人类直立行走后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让两只“手”空闲出来。闲而无用,方成“大用”。空闲的前肢让鸟类演化为双翅高飞,人类则发展出奇巧的双手。有了万能的手,人类才可能成就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大作为。人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前爪”,它的四指全都朝向一方,唯有“大拇指”低位斜出(甚至指向垂直)。有了“大拇指”的特异分化方可与其他四指精妙合作,成就了可以灵巧制作各种人工制品的“双手”。此指“异象”,连指骨都比其他四指少了一节,足见不凡。特殊的双手使得人类堪称另一个“造物主”,在地球上逐渐创造出了一个适宜人居的人工世界。
语 言
人类拥有语言之日即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揖别之时!
要想形成语言,首先必须具备抽象识别能力。唯有抽象出某些事物的共同特征,才可以把它们归为一类。有了归类才可以给这类事物命名,从而产生一系列可构成语句的各种名词、动词。可见具备抽象识别能力乃是产生语言的前提。
人类语言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那种本能发声。所有大型哺乳动物的喉都长在喉咙的高处,这使它们可以同时喝水与呼吸。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的观点是:“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又据杰弗里·莱特曼等人的研究:“扩大咽部乃是实现清晰发音,扩展语言范围的关键。”对人类而言,喉的降低虽然让人类独得了一个大音室,但带来的副作用是喝水时必须屏住呼吸。只是婴儿无知,不懂这种转换操作。为此,造物主特别眷顾婴儿,让其出生之时也像典型哺乳动物那样,喉处在喉咙的高处,可以同时呼吸与饮水,哺乳才得以实行。18个月以后,其喉向着咽喉下部移位,14岁时到达成年人位置。
人类语言的另一个特征是人脑中具备特殊的语言模块!所有人类大脑里都有共同的“语言模块”。当今世界几大语系共有林林总总6000多种语言。尽管人们语言各异,但众多语言之间却全都可以互译。人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所有人类语言中都存在着共同的语法。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认为:“婴儿出生时,脑里已设定了基本的文法规则。否则你怎么解释为何世界上每种语言都有一个共通的文法模式?”语法是极其重要的,“若懂得造句语法,仅凭几百个单词便可表达数百万种不同的含义”。
语言的产生还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达。考古学业已表明,人类的脑容量在20万年前曾经有过一次突然的增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语言的诞生。语言交流使得信息量猛增,让人类大脑由最早南方古猿的400毫升增加到现代人的平均1350毫升,脑量增长了3倍。
语言区位于大脑左半球的布罗卡区,故语言发达会使大脑的左半球略大于右半球。考古学家在约200万年前的“能人”头盖骨中不仅找到了布罗卡区,而且确实发现脑的左右两边稍稍出现了某些“不对称”迹象。此外还有一个证据,由于人类现代语言需要一个特大的“音室”,喉的降低会使头骨的“颅底”呈现拱形弯曲。考古学家发现,充分弯曲的颅底最早出现在30万~40万年前远古智人的“化石脑”之中。
正是因为人类先天地具备了共同的低喉器官和语法模块,各种语言可以互学互译,才使得世界上任何区域性信息都可以转化为全人类的共通信息,从而保证了人类的信息相通。
可以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一切人类文明。整个人类一旦失去语言,文明传承也就难以为继,不出百年,人类文明大厦就会彻底崩塌!呜呼,人类文明竟然虚悬于“语言”一线矣。
如是观之,“语言”自可视为一种“判据”!拥有语言(包括体语)方可以视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同医学将完全没有知觉的人称之为“植物人”,那些完全没有人类语言的健壮“狼孩”似可称其为“动物人”。
思 考
帕斯卡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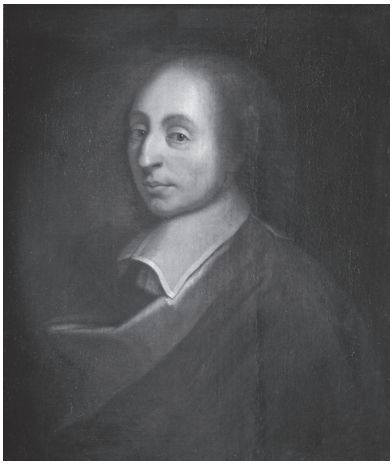
图1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布莱士·帕斯卡
人为什么会思考?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具备思考能力?关键在于人类拥有语言!
思考必须借助语言!语言除了让人类群体彼此交流信息外,更可以让个体进行自我思考。思考就如同是一连串自言自语的无声语言在头脑中默默运行。这种无声语言可以看作是思想的“载体”,没有语言承载就不可能进行逻辑思维,更不会产生思想。
语言的“思考”功能也许更重于它的“交流”功能。因为思考乃是人类认识之源头,交流只不过是彼此间的互通有无。先有“源”而后有“流”,“源”永远是第一位的。
人类之所以要思考,至关重要的是——人类对“未知”现象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区别的是:人类本能的有一种“探究欲”(见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这种探究欲使得人类每当遇到新奇事物时总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总想问个为什么,还会使用语言将其在头脑中反复琢磨,直至悟出可以完满解释的答案,并在经受不断的检验之后构成人们新的认知。一次又一次认知的积累,使人类对周围事物形成了越来越深切的整体性认知。科学研究就是专门从事“探究”的事业,“研究”而不见“未知”,就等于没有摸到科学的“边”。
就未知事物的认知而言,相比于逻辑思维,源自于直觉、顿悟的悟性思维常对悟得新知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东方文化用“脑”思考,用“心”感悟,最具整体性“综合”眼光,“悟性”——这种最高级的大脑活动也就寓于其中了。与逻辑思维相比,这种不完全依赖语言的悟性思维乃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悟性思维能力的强弱也是衡量一个人才智高下的首要依据。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领悟,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对基本定律的归纳以及哲学自然观的建立几乎全都来自悟性思维。
信息只有当其用作于思维之时,方能充分发挥出其内在的潜力。当思维使各种信息产生交互作用时,必然会创生出更多、更本质的新信息,这是一个2+3远远大于5、大于50、大于500的信息暴增过程,它体现了信息所深蕴的巨大生命力。例如,门捷列夫根据当时已发现的几十种元素,将其各种化学性质一一写在纸牌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排列组合摸索,最终发现“元素性质依据原子序数的增加而显示出周期性变化”,从而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显然,“化学元素周期律”所含有的信息量远比单个元素那些零散的孤立信息量有着千百倍的增加。
“思考”不仅使信息充实“现在”,还可使其容纳“未来”。
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70多年之后,原子结构的研究让人们确切地知道了“电子满壳”结构。这一理论清楚地指明了原子壳“外层电子数”对元素的化学性质直接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揭示了“周期律”的微观本质,将其更深层次地纳入元素周期律的信息之中。
遗传定律的发现也体现了这种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相互对映。分子生物学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使得孟德尔通过种豌豆所发现的遗传定律与摩尔根通过养果蝇所创立的基因学说都在微观层次上得到了最确切、最本质的完美阐明。大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各种不同层次的信息都会是相互印证、和谐一致的。这充分体现了信息的内在贯通力。
交 流
信息的天然品格就是交流!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往往是“信息”决定“规模”。信息交流达到多大范围,人们也就能够协同统一到多大范围。“信息”整合的规模越大,思考交流得越深切,“智能”也就越发达。
“全息”乃是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特征。如同一张印在玻璃底板上的全息照片,哪怕摔得粉碎,任取一小块碎片在激光映照下仍旧可以得出与原来底板分毫不差的整体图像。人类最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所得到的“新知”通过信息通道汇聚到人类的整体文明之中,成为人类的“全知”;这种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知识又可“全息化”到人类的每一相关成员之中——个体存在于整体中的同时,整体也全息地寓于每一个体之中!这很像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信息又都寓于人体每一个细胞核的DNA之中。人类的文明信息如同一个“聚宝盆”,它只增不减,越聚越多,任君自取,却不减分毫。
似乎只有数学上的自映射集才会有这种无穷无尽的自嵌套现象。如同你在头的一侧肩上树立一面镜子,然后再去照一面大镜子,镜子里固然有你,但整个镜像又映照到头侧的镜子里;它又再次回映在大镜子之中,刹那间层层反复映射,直到无穷。这越来越小的每一面镜子里都含有同样的信息。人类文明也同样可以层层“嵌套”地存在于全人类、民族、国家、地区、大学,直至个人之中。
“全息”之所以形成,就在于“信息可以共享”这一信息内在本性。“人”是一种必须以整个人类文化作为依托的“社会化生存”,不存在任何可以与这种联系完全隔绝的人。
信息需要“储存”。人脑不仅能够创造信息,还能够储存信息。“回忆”就是调取头脑中存储的信息。一位老人与一只老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老人可以按照人生履历追忆平生,而老猴却不可能有“回忆录”。有“回忆”方知“自我”!“我”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完全“失忆”之人甚至全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于物种而言,智能没有“中间过渡态”。这很像二进制的“1”与“0”,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在当今世界里,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拥有智能的物种,冥冥中似乎还存在某种智能“断后”现象——人类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任何智能物种。几百万年前的原始“能人”,若将它们与当时的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相比较,在智能上也不过是略分伯仲叔季,并非天差地别。现在却有如高崖顶上垂下一架“智能天梯”,排在最前面的人类爬上去了,天梯也随即抽回,排在后面的几种类人猿再无爬上去的可能,只好望崖兴叹。不过这也怨不得别人,谁让它们没有语言,不会思考,疏于交流,缺乏广泛的社会生活积累呢。尤其是,没有语言,一切归零!
按照《人类的近亲》一书所描述:与当时人类大脑容量不相上下的黑猩猩本为素食,“它们外出觅食一般一只或几只雄性黑猩猩和一只携带子女的雌性黑猩猩结伴而行。这种六七个成员的小家庭式生活使得它们与其他同类很少交往,几乎没有社会生活,更无法在更大范围中进行交流,因此也就不可能积累较多生活经验”。若从DNA分析,纵使经历了百万年的分道扬镳,今天的人类与这些现代类人猿的基因组差异也不过是1.6%,但在智能上却已是天壤之别。
DNA只能遗传身体结构信息,而人类的文化、知识、经验等“后天”得到的精神信息并不在“遗传”范围之列(若是学问能进入DNA,哲学家的儿子生下来就精通数理哲学,数学家的儿子一落地就通晓“微分几何”,还会是今天的世界吗?此种谬误倒很像是生物“获得性遗传”的拉马克学说)。每个婴儿不论出身贫富贵贱,出生之时都如同一台清空了的电脑。造物主在智能知识方面绝对公平,它让每个初生儿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农业定居使群体密集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
人类真正的社会化生存首先从“定居”开始,唯有定居才有可能实现群体密集的信息交流。
人类的定居发端于野麦的种植。1.2万年前,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附近的人们耕种了一种“一粒系小麦”,这种野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麦粒不像其他麦种那样边成熟、边散落,让人无法一体化收割。利用“一粒系小麦”具有的这点“延迟时间”使人们得以对它集中收割、脱粒,制作面包等。正是因为有了农业才使得人类与“农田”相依为命,并从此开始了定居的农耕文明生活。农业靠的是“循环增殖”,种出来的麦粒除去留种之外,多出来的部分才是“粮食”(就像银行储蓄,本金不动,只提取利息)。
只有群体规模达到足够大时才可充分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卡尔·齐默在《演化》一书中说:“根据邓巴对灵长类脑部的研究,脑部的扩大必定和人类社群愈变愈大同时发生”。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克尔斯在《脑的进化》一书中也说过:“一个社区内的人口可能必须达到一定的临界阈值,这样,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彼此间才能有所互动。”聚居在一起的人们“信源”丰足,“信道”便捷,“信宿”众多,在“信息三要素”方面独占鳌头。唯有聚居才能集中地进行信息交流,而且聚居规模越大,信息交流也越频繁,文化发展得也就越快。农耕文明使人类得以定居于农村乡镇,工业文明又使人类得以在更大规模的城市里安居。幅员广阔的城市信息交流让科学、哲学、教育、传媒、艺术、宗教等均得到了综合发展,为引发人类文明新的爆发积累条件。相比之下,居无定所的游动性狩猎与采集(甚至包括历史上强大的游牧民族)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交流与积累,也就不可能产生全面的现代文明。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唯有农耕文明才真正开始了人类的文化进化。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生生不息地总共生活过800亿人,其中88%的人都生活在这一万年里。此前的几百万年只不过是文化进化的序幕,最近这一万年才是真正的大幕拉开,以后将是一幕幕恢宏壮阔、愈演愈精彩的文化正剧。
文 字
几乎所有古老民族都拥有跟自己语种相对应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凝固了的语言,本质上还是“语言”。文字的出现让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相比于几十万年前就已形成的现代语言,有文字的历史不过6000多年。文字出现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的远古时代只能称作“史前”)。可以想象,在“前文字时代”人们结绳记事,所有信息只凭口耳相传,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一个百人部族之中,不可能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交流。

图2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
文字和语言虽然都是信息的载体,但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时空”。单纯的语言只能成为一种瞬间即逝(声速340米/秒)的近距离传播,并局限在狭小的时空里发挥作用(不包括100年前刚刚发明的电话和此后相继发明的录音、录像)。相比而言,文字却可以拥有无比广大的时空。人类若是需要一种能够长久保存并得以在全人类范围内进行交流的信息载体,那就必须要有“文字”!没有文字的“固化”信息,绝不会有今天的文明世界。
这或许是个规律——人类最发达的早期文明几乎都拥有自己的文字!如两河流域古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一份农牧业账单距今已有6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圣书文字”(距今5000年);华夏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用于占卜,距今3300年)。这三种重要文字已被周有光先生称之为“三大古典文字”。除此以外,还有古希腊字母(公元前11世纪)、古印度婆罗米文字(公元前7―8世纪)、古玛雅文字(428年―16世纪)以及古阿拉伯文字等。
拼音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声符号”,这些“词符”本身并无意义,唯有看到这种符号并直接转化为“声音”时,人们才知道它的语音含义。拼音文字更像是一张“录音纸”,将语句的“读音”记录在纸上,随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按照原来记载的语言声音直接读出来,从而摆脱了语言本身的时空局限。
人类还有一种“记声符号”,那就是西方的五线谱(中国人则有自己一套用方块字记述的乐谱系统,即“工尺谱”)。谱写音符的五线谱纯粹是声音的流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用它来表达人间的喜怒哀乐,不着一字却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一曲恢宏壮阔的《命运交响曲》绝不亚于一首激扬文字的壮丽诗篇。
字母文字与语音一一对应,然而,与其大相径庭的方块汉字却可以相对独立于“语音”。其字形本身就含有某种特定的意义,你也可以只从“图形”上来认知它,哪怕不知道它念什么(读白字、错别字都行),甚至不同地区均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方言声调来读它。方块汉字还独有“六书”概念(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从甲骨文一直贯穿到今天的楷书。
文字需要“载体”。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记录在陶泥板上;古埃及人把圣书文字记录在纸莎草纸上;中国人把方块汉字记录在甲骨、简牍、帛书,以及汉代之后的“中国纸”上。
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8年第3期。
《科普创作》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刊,以刊登科普科幻原创作品及评论为主,刊物为季刊,每年3月、6月、9月、12月的20号出刊,欢迎投稿订阅。投稿邮箱:kepuchuangzuo@126.com;联系人:姚利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