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困惑” 开创科幻新天地——学习洛特曼人类文化符号学著作札记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孟庆枢 2019-05-10 20:57
当前我国科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火爆银幕,以及《天火》荣登日本顶尖文学杂志《三田文学》(今年春季号,4月10出版),从而成为日本国际科幻专号唯一的中国科幻入选作品,并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国内各界对于中国科幻给予了更大的期望,预示了中国科幻的美好前景。

但是,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科幻界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困惑,甚至对何为“科幻”也越发感到不得要领。刘慈欣在2018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了“科幻”内涵的变幻莫测,并提醒创作者们不要跟风式地摹拟某种形式。对于他这番讲话的反响,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先后于2月6日和2月8日两次同他电话交谈,深知他的这些想法是结合当今国际上科幻发展实际的中肯之谈。这里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何为科幻”。如果我们把国际上的科幻现状和我国当下科幻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他的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要想迎接中国科幻更美好的明天,必须破除这些困惑。
这里,我想从人类文化符号学的视点略谈一二。
虽然人类文化符号学是显学,但与科幻联姻尚不多见。一位大师级人物——前苏联理论家洛特曼(1922-1993),他的经典著作在国内至今尚无从俄文直接译介的版本,而这些经典著作对于当今文学、艺术的重要价值决不低于许多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无论谈任何文学作品,他最突出特点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学、文化观,坚持把“人”作为整个“文本”网络(内与外结合)的有机整体构成,提倡人文情怀与自然科学理性更好融汇。洛特曼认为,诗的语言(包括科幻小说的语言)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它和其他所有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些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形形色色固有的语言如影随形。冬尼亚诺夫将它命名为“系列”。比如说日常语言系列、世态风俗系列、社会系列等等,这些系列又是彼此相关,这些相关联的层次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从素材即可窥见在作品里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诸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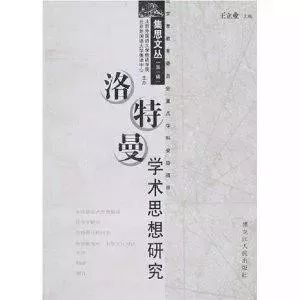
文学文本就是各种语言的织物。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出现的作品形式永远不变,但是它的机能已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发生变化。比如,洛特曼在1970年说过,现在是科学时代,科学系列的现实性可从科幻小说的昌盛里得知其反映。这就把科幻作品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都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体现来思考和进行阐释。
日本一位洛特曼研究家(也是洛特曼著作翻译者)磯谷孝在洛特曼的代表著作《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一书的翻译“后记”里,结合洛特曼的理论指出:“从信息理论来说,世界乃是形形色色的信息过程的总体。主体接收作为现实意味的信息,并且发送这些信息以适应环境,以求保存自己。这也就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对于科幻是否也可以先从这一视点来思考呢?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思考。
早在20个世纪30年代,在西方哲人中如海德格尔就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观念,他把艺术创作理解为一种生产(Hervorbingen),他提出“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言说中栖居”。海德格尔把天、地、人、神作为一个网络来对待。置言之,只有让“人”重归于“人”的坐标,才能让他有生命力,不然就是自我“神化”,其实也是虚无化。笔者认为,一切文本都是人的生存意识、求新创造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和回归意识的诗意体现,科幻文本同样如此。
这里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科幻小说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对“文学”的“越界”。其实人类生活在原本并不存在何为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共生呢?它们必须是互补互助,但同时也是矛盾的统一,并非是静止状态下的共存。整个宇宙是个动态的整体,运动(矛盾)是贯穿一切的,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文学艺术必须承担起制约、调整科学技术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任务。同时所谓的人文思想也必然是你与时俱进的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融为一体。在当代社会,科幻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当时,洛特曼将前沿的自然科学理论引进人文科学之中,还特别关注了当时新出现的控制论、信息论、量子理论,对一些文学经典作出了最前沿的再阐释。他借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克尔玛戈洛夫,从统计学角度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进行文本阐释(1963),进而论述了熵与文本的关系。洛特曼认为,克尔玛戈洛夫的熵与文本的研究很有价值,针对“符码”里的不同层面的“熵量”,“作者符码的熵量与读者符码的熵量的不同”的研究,“开拓了文本里诗与研究中统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科幻文本,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也呈现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结合熵与文本的研究,可以作为个案。洛特曼援引克尔玛戈洛夫院士论述指出,语言的熵量(H),有两种成分组成:H1,即语义的容量,传送一定长度的文本中的语义信息的语言容量;H2,即语言的灵活性,由几种相等的手段,传送同样内容的可能性。
克尔玛戈洛夫院士指出:“语言的熵由两个值构成,一个是一定的意思容量(H1),它也可以叫做语言在一定的长度的文本里传达某一信息内涵的能力。另一个是语言的融通性(H2),是同一的内容用几个等价值的信息来传递的可能性。在这时,成为诗歌的信息源只能是H2。当H2=0时的语言,比如排除掉同一表现的可能性的学术语言,就不能称为诗的素材。”
洛特曼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科幻文本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科幻作品中自然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诗歌语言)的关系。如果科幻作品里满是科学术语,那只能是自然科学教材或科普书。它必须融合艺术语言“披优孟之衣冠"以达”析理谭玄”的作用,才能在一个新的文本中讲一种别样的故事。过去一直争论的科幻文本中的“硬”“软”之别,莫衷一是。如果从熵的角度来思考,我想科幻不必拘于“软”“硬”,核心在于它必须让读者有想象、再创造的空间。
科幻文学既要区别于科学科普作品,也不同于毫不介入科学的某些虚幻作品。为此,我国许多研究者、科幻作家的“科学+文艺”的表述,如果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融会贯通,那是有道理的。同时,洛特曼也指出,同一文本的熵量在作者和读者那里是不同的。如果对有自然科学含量的科幻作品毫无必要的科技知识储备,那么读起来会如坠雾中,或者跳过去,或者查找资料再读。当今的教育已处在重视综合性的时代,侧重自然科学的读者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的读者要相向而行,由此受众将会不断增加。
文艺作品在传达信息量,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内涵上,并不弱于一般的自然科学著作。洛特曼以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为例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让读者把契诃夫的中篇小说与心理学教科书进行比较(见俄文版第35页)。他没有提及具体作品,我们不妨拿《没有意思的故事》这一中篇为例。众所周知,契诃夫在医学专业上也是佼佼者,他的许多作品,如果没有坚实的医学知识,是达不到独到、深刻的。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副标题是“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教授尼·司捷潘诺维奇是主人公,他的心理活动贯穿故事。在小说中,契诃夫把经典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医学、心理学融会其间,让人步入心灵世界的奥堂。洛特曼指出:“在很短的文本的‘场’中容纳了庞大的信息量,这就造就了艺术文本的一个特性,而且它还具有对不同程度的读者提供不同信息的能力,即适应不同程度的读者给予不同的信息,进而使读者常读常新。于是作者和读者就形成一种反馈关系。”(见俄文版第35页)
这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艺术和人的精神需求的奥秘。人们可以在艺术与自然科学文本里接受不同的信息。但是必须是艺术文本的“场”具有活力,让读者历时地参与共创。自然科学话语的选择,也必然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文学作品有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的思维模式的改变,而不仅是知识量的多少。
洛特曼的著作里还论述了量子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显然更前沿,另有专文论述。当今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也许从这个原因说,从科幻中寻找科学发现的灵感与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科幻是变化的“九头鸟”,更是“跨界生长的精神树”。只要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旨在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互联网+”时代,用新的方法讲好中国科幻故事,就会开创中国科幻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孟庆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大学孟庆枢学术中心


